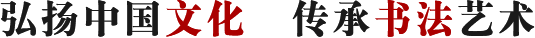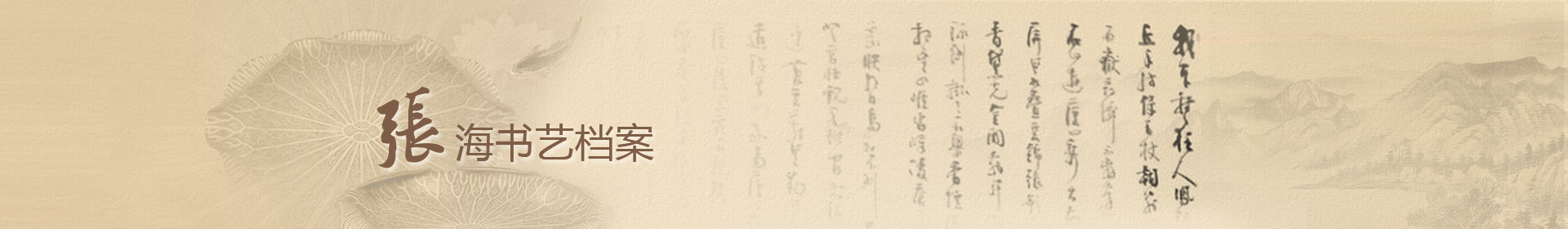一、行草书发展概况
关于行草的名称,大约起于“稿草”,南朝萧子良云:“稿书者,董仲舒欲言灾异,稿草未上,即为稿书。”三国韦续说:“稿者行草之文。”(清刘熙载《艺概·书概》)这大概是最早出现的关于行草的说法。唐张怀瓘《六体书论》说:“行书者,刘德升造也。不真不草,谓之行书。晨鸡踉 而将飞,暮鸦联翩而欲下,贵其家承蹑不绝,气候通流。逸少则动合规仪,调谐金石,天姿神纵,无以寄词。子敬不能纯一,或行草杂糅,便者则为神会之间,其锋不可当也,宏逸遒健,过于家尊。可谓子敬为孟,逸少为仲,元常为季。”
张怀瓘的这段话有这样几个意思:一是行书的创始人是刘德升,行书是介于真书和草书之间的书体;二是行书的特点是充满动感,气息畅通;三是王羲之为行书树立了优秀典范;四是王献之的行书严格讲并不纯正,而时常把行书和草书杂糅在一起,然而其天然得意之处,往往超过其父;五是行书成就的排名应该是王献之最高,羲之其次,钟繇第三。
张怀瓘的说法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为后世书界所认可,清刘熙载在《书概》中说:“行书行世之广,与真书略等,篆隶草皆不如之。然从有此体以来,未有专论其法者。盖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详,知真草者之于行,如绘事欲作碧绿,只须会合青黄,无庸别设碧绿料也。”
对草书的论述,在古代书论中比较多。张怀瓘说:“草书者,张芝造也;草乃文字之末,而伯英创意,庶乎文字之先,其功邻乎篆籀,探于万象,取其元精,至于形似,最为近也。字势生动,宛若天然,实得造化之姿,神变无极。”草书贵在从自然中取象,因此其精神最符合“道法自然”的宗旨。蔡邕所谓“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草书虽有文字规范,但写法各人不同,因此最能反映人的个性、襟怀、志趣,故此又有“草无定法”的说法。刘熙载说:“书家无篆圣、隶圣,而有草圣。盖草之道千变万化,执持寻逐,失之愈远。非神明自得者,孰能止于至善耶?”草书人人能写,然而要写出神韵,写出境界,确非易事。
据史料记载,草书创于张芝,而且据说张芝的草书是连绵不绝的一笔草,只是张芝的墨迹没有留下来,《淳化阁帖》上所谓张芝的草书是后人伪托的。王羲之、王献之也都善草书,王羲之的草书字字独立,被后人称为小草,而字体连绵不断者称为大草。著名的小草书家和作品还有智永的千字文、孙过庭《书谱》以及怀素的《小草千字文》等。练习小草,对于熟悉和掌握草法是十分必要的。
唐朝张旭、怀素创狂草,狂草比大草更奔放,更有气势,字形更加简约,乃至难于辨认,然而仔细分析,狂草的字法又很严谨。据说张旭和怀素都嗜酒,醉后兴致高涨,有一种“酒神精神”,在高度亢奋的精神状态下,写出来的狂草如大河奔流,一泻千里,极有气势。张旭与怀素相比,二者虽都是以气势取胜、狂放型的草书大家,但在用笔上又略有不同。张旭用笔变化丰富,重提按,而怀素用笔偏瘦,提按较少。黄庭坚说:“怀素草工瘦,而长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劲难得也。”张旭《古诗四帖》、《忽肚痛帖》,怀素《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等至今仍是习草者的优秀范本。
宋代草书,以黄庭坚成就最高。黄庭坚用笔主要师法张旭、怀素,又参用了二王、智永、杨凝式的笔法。加以侧锋取妍,主张“字中有笔”,即在线条中表现笔的提按正侧变化。《诸上座帖》、《李白忆旧游诗卷》、《廉颇蔺相如列传》是黄庭坚草书的代表作。
元代草书以鲜于抠为代表,用笔精到,气象开阔,具有很浓的书卷气息。明代草书成就很高,大家辈出,徐渭、祝允明、王铎都有很高的成就。其中以王铎成就最高。王铎草书,打破以技巧取胜的传统用笔,强调用笔的自然、质朴,他把篆隶的用笔引入草书,线条生涩厚重,雄健有力。同时王铎草书的墨色变化也比较丰富。王铎草书多大幅作品,和今天的书法表现形式更为接近,因此也更便于临摹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书法热,催生了各式各样的展览、比赛。但直到2005年以前,行草书是没有分开的。这大约是因为行书和草书本来关系密切,很多作者在创作上是二者兼及的。在一幅作品中,兼用行书和草书技法更是随处可见,传世的行书经典之中也掺用许多草书,因此人们在概念上往往把二者当成一种书体。2005年中国书协换届之后,按书体设立专门委员会,才把行书和草书作为两种书体分设。这是基于这样几种考虑:一是二者虽有很高的关系度,但毕竟不是一种书体,有各自的发展规律和特定内涵,作为专业委员会,应该分别进行研究考察。其次,在展览、比赛中分书体进行,有利于更公正、更客观地评价,一幅典型的草书和一幅典型的行书在艺术上是很难有可比性的;再次,把行书和草书分开,利于引导书家对两种书体分别进行更深入更精细的研究,尤其是对于纯草书的研究,意义更为明显。
专业委员会虽然分开了,而且各专业委员会都举办了各自的展览,但在很多场合下,大家还习惯把行草书放在一起来考察,而且在一些综合性展览中,也不便把二者分得那么清。因此我在这里也把行草书放在一起来谈。
二、我的行草书创作轨迹
我的行草书创作,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以1992年第五届全国书法篆刻展为分水岭。
我学习行草书的时间,与隶书同步。一般来说,不论从实用,抑或创作,倘若起步即专注于楷隶篆,都应当同步学习行草。因为以这三种书体创作的作品,落款用行草书最宜。楷书作品落款可以用楷书,但篆隶作品落款最好不要用篆隶书。如此算来我学习行草书也有几十年了。现在回过头来审视行草书创作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从初学书到一九九0年,数十年间,处于寻觅阶段,从自己爱好出发,不断地取,不断地舍,如同方砖铺地,涉猎较广阔,但始终缺乏高度,尽管行草书作品早在一九七四年就入选河南省书法展览,但我自己认为,没有自己的风格和专注的追求而显得平淡无奇。
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像许多初学者一样,缺乏名师指导而掉入学习当地名家的陷阱,以模仿一方之秀为能事。我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认识费新我先生后,写过一段费新我先生。费老左笔作书,走的也是碑派的路子,以气势、线条的质感以及通篇的整体效果取胜,而不是斤斤于点画的精到细腻。这些都与我的审美取向相符合,因此学起来特别容易上手。
但写了一段后,我自己也就不再写了。原因一是意识到步趋时人怕落入某种窠臼。尤其是后来与费老交往渐多,老人家赠我很多字,我虽然很喜欢费老的字,然而倘以此面目示人,岂非有抄袭之嫌?二是八十年代初曾在两次大展中受挫,使我猛醒。一是我写了一幅大字行书对联“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自认为写得很好,就向上海《书法》杂志投稿,结果未被采有。二是一次展览,我又投了一件有费老影子的作品,虽然几位同道认为写的不错,但又偏偏没有入选。这无疑是给我敲了一记警钟,看来这个路子是不能走下去了。然而出路在哪里呢?经过认真思索,我自己得出的结论是:还要从古人那里寻找答案。心存侥幸,希冀有成,不从经典入手,也许会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但最终结局只能是徒费时日。还得从头越。话又说回来,即使入手经典,也不一定都能心想事成,但要想从心随愿,这是一条不是捷径的捷径。
在诸多古代书法大家经典作品中,我比较喜欢怀素《自叙帖》,临习有年,从怀素那里我不仅学到了草书的字法,而且在用笔使转、线条遒劲方面也得到了很好的训练。然而在练习中,我也渐渐觉得怀素的草书虽使转流畅,但在气势的雄浑苍劲方面似嫌不够,要想直接以怀素书法风格去创作具有现代气息的作品,难度很大。1983年,河南省书协与日本王铎研究会共同举办了“王铎书法展”,展出国内和日本收藏的王铎作品40余幅。此展在全国引起轰动。王铎草书以气势胜,洋洋洒洒,磅礴恣肆,不但弥补了怀素的不足,而且为书法从案头走向展厅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借鉴。
从怀素到王铎,使我的行草书形成了以雄强浑朴、畅达恣肆为主要特征的风格定位。然而要想在国展这样的场合脱颖而出,似乎还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
由于经常参加展览的评选工作,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我发现一个现象:在全国性的大型展览中,往往是行草书多,楷书少;而在行草中,又是大字、中字多而小字少,尤其是接近楷书的小字行草,以及古人手札风格的作品样式可以说是少而又少。我想,个中原因恐怕主要还是这种小行草创作起来有相当难度:年轻人功力不够,下笔难以精到;老年人目力不济,落纸又难求细微。以我当时的年龄和功力,自认为还是有优势的。这时我想起自己1970年在荣宝斋学习时,时常用装裱余下的边角料写小字隶书,效果相当好,创作的柳宗元的“封建论”1974年入选河南省书法展。想到此,顿时开悟,何不从小字行书入手呢?于是就试着用这种形式进行创作。一些朋友看过我写的草稿,都连声说好。1990年“河南书法周”在北京举办,我写了一件小字行草作品,王学仲先生看后大加赞赏,让吉欣璋先生给我捎话说:“这条路子选得很好,展出的作品典雅,很有书卷味,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这使我更加坚定了走这条道路的信心。
自信是建立在对自己的客观认识和科学评估基础上的,十足的信心是冒险的基础和前提。艺术家和冒险家都有成功和失败两种结局,探索是冒险的尝试初步,在学习书法到成名的漫长过程中,自信冒险或许是走向成功的一跃。
1992年全国第五届书法篆刻展,我决定用这种风格小字行草投稿。早先曾在香港买到一批台湾产的宣纸,这些纸质类布纹,看起来粗糙,但写起来既有陈年好纸的润泽,又有新纸的生涩,很适合写小行草,便用四尺对开纸写了现代诗九首。寄送前周俊杰先生看了,他认为作品很出色,并断言能获奖。作品投寄出去后,我正好要出国。往届我是评委,评委的作品可以直接入选,但不能评奖。但这届评选我不能参加了,作为一般作者投稿,自信中不免忐忑,不知作品命运如何?结果我出国访问刚到家,消息传来:作品以高票获奖。
其实我这次投稿是冒着风险的。老伴劝我为求稳起见,还是投隶书的好。当然老伴说的是有道理的。投隶书即令不获奖,入选应当问题不大。而第一次以这种风格示人,落选风险较大。因为这次如果落选,别人自然会说,张海一不当评委,作品连入选也入不了,言下之意,以前的作品入选也不过是评委的特权而已。但后来反复权衡,还是决定搏一下,因为如果这次能过关入选,也能说明很多问题。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如果处处患得患失,首鼠两端,可能最后什么也得不到。
五届全国展作品获奖,使我坚定了信心。我觉得对小字行草这种书体的认可,其获奖意义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对自己探索精神的肯定。
有了这次经历,心中便有了底。我想,小字的感染力毕竟有限,难以充分表现展厅效应。可以作为一个品种,但不能守着一种形式不变。有一种笔名字叫做“小大由之”,我想在书体上也应该做到小大由之。于是除了小行草之外,也陆续创作一些大字行草作品。当我放开创作大字行草作品的时候,忽然意识到,怀素对我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而且过去下功夫临过的王铎以及二王若干经典,都能发挥作用,在创作中使转纵横,畅达自如,以及顿挫的节奏、字形的结体等等。这使我体会到:首先,临池的功夫是不会白下的,当时可能感觉不出来,但积累下来的功力沉淀在你的潜意识里,在适当的时候它就会表现出来。好比一个人做了助人为乐的事情,事后可能自己已经忘了,但别人还一直记住,不知在什么时候,他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来报答你。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吧!其次,书法家的风格定位,不可能完全按照事先的设计发展,而是一个边探索边修正,趋利避害,披沙拣金的动态过程。重要的是不断探索思考,不怕遇挫折,不怕走弯路,不断给自己提出更高的目标。
作品集是一个艺术家阶段性的总结与回顾:若干年后审视当年自己认为满意的作品,或许汗颜,或许幼稚,或许惨不忍睹,但这都正常,这是自己眼高的表现。危险可怕的倒是事隔多年,看到这些作品仍然沾沾自喜,洋洋得意。不怕幼稚,就怕一直停留在幼稚的阶段。
1995年,河南美术出版社为我出版了第一本综合性的作品集《张海书法》。(以前曾出版过《隶书两种》单一书体的作品集)沈鹏先生看了集子里的作品,给予充分肯定。他在飞往新加坡访问途中写下了《创造力的实现》一文,对我的隶书和行草书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尤其是他对我行草书的评价令我感到意外。他说:“倘若观者不限于‘先声夺人’的定见,他那近二三年来的若干行草书新作水平实际上超过了早些年的隶书。”沈老并说:“在创作中发现新的东西要赶紧肯定下来,成为风格中相对恒定的因素,然后再充实,再发展”。沈老的话特别符合我的想法,因而我对自己的选择也更有信心了。关于我的隶书,沈老在文中表示“偏爱那幅四尺中堂《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兼寄语弄房给事>》,认为这幅作品“让你分辨不出笔画的来由”、“用笔如屈铁,如游丝,布局成行不成列,萧散又严谨,空灵又凝重。”沈老还特地对我说能否为他写一幅。其实这幅作品自己现在看来,除了形式上尚有些可取之处之外,其它方面就平平了。总之,这第一本作品集,现在看来虽有点令人汗颜,但在当时,也算是一次收获吧!
虽然第一本作品集不尽如人意,但在创作的过程中,毕竟从中悟出了许多东西,明确了今后着力的方向。在创作中印证了许多过去在书本上学到的理论,边创作边感悟,从而使自己逐渐从盲目走向理性。比如唐代孙过庭曾提出:“五乖五合论”:“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循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对此我有很深的体会。
创作中,我曾搬进宾馆,试图摒绝杂务,排除干扰,把一个时期的艺术积累和创作冲动全部释放出来,然而却事与愿违。我发现写完一幅作品之后,再也无法写第二幅。这有点像钻探,钻到一定深度,钻头发热,不能再继续深钻,必须冷却,而冷却的时间有多长,又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并无定规。可知创作是一个可遇而不可寻的自然而然的过程,正如孙过庭所说的“神怡务闲”、“偶然欲书”,往往能出好作品,而在精神上、体力上准备不足,强令自己进入创作状态,这就是孙过庭所说的“心遽体留”、“意违势屈”,怎能写出好作品呢?无奈又从宾馆搬回家中。
从此事中我悟出以下几点:
一、成功的艺术创作是这样一个过程,它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必然性是平日的积累和准备,以及强烈的创作欲望,而偶然性则是合适的时机和条件,没有平时的积淀和创作欲望,即使条件具备也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但仅有创作欲望,没有适当的条件和契机,也出不了好作品,二者的关系如何把握,这就要考验书家的智慧了。
二、艺术创作不是匀速运动,而是经常会出现飞跃期,飞跃期的出现要靠平时的积累、探索,寻寻觅觅,这是一个必要的准备过程,有了这个过程,一旦时机成熟,飞跃期就会到来。这种时候,书家有可能进入一种匪夷所思的颠峰状态,创作出平时不曾企望的优秀作品出来。
三、成功的书家必定有自己的目标和计划,没有目标,没有计划,完全靠碰运气去搞创作当然不行。然而成功作品的出现往往又是不可预期的。平时看似漫无目的的寻寻觅觅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寻寻觅觅看似漫无目的,实则是寻求突破口,是打迂回战,因为占领制高点并非总是靠正面抢攻。总之创作既非按图索骥,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失败甚至多次失败的思想准备。但无论如何这个过程是书家全身心投入的结果,好比董其昌所说的“狮子捉象”,非拚尽全力不可,乃至成功之后,身心俱疲,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可能是艺术上不可重复的“这一个”。
我的行草有多种面目风格,虽然从技巧上来讲差别很细小,但总体上给人的感觉差别是不小的。这并不是随意生发的结果。首先是长期地积累和探索的结果;其次来源于不停的实践;再者也有一点与生俱来的驾驭能力和自信。我比较注重灵感的捕捉。对于有心人来说,启发灵感的契机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如朋友交谈中某句话的启示,听音乐时某种旋律的联想,甚至一个梦境等等,都可能启发创作的灵感,并且能形成某种特定的风格面貌的雏型。久而久之,这种生活中捕捉灵感用于创作的习惯也就成为一种能力。我觉得对一个书家来说,这种能力的修炼是必要的。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多年苦苦追寻自己行草书创作样式终于在2003年创作的《苏辙(黄州快哉亭记)》得到契合。从此一发不可收。沿着这一思想不断向广深延伸,在延伸中又反复调整修正,这条路究竟能走多远我也不知道,反正八年后的今天仍无改弦易辙的想法……
进入新世纪以前,我没有举办过个人展,2000年以后,就想办一个像样点的个展,经过了几年准备,愿望终于实现了。2004年7月1日,首次个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
书法展和画展相比,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书法从造型、表现内容到色彩运用,都无法和画展相比,绘画可以直接表现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和自然风光,造型丰富,色彩多样。而书法的表现对象无非汉字而已,充其量多写几种字体,色彩更是单调到白纸黑字加红色印章,因此书法展要想出彩绝非易事,想激发观众的兴趣和激情则更是难上加难!
书家要想办好个展,起码在三个方面要经起观众拷问,一是要有至少两种立得住的看家书体;二要有若干件让观众眼睛一亮之后又认可的作品;三是装裱整体设计有不同凡响之处。显然,书家能擅长几种字体并非易事,如要求画家同时擅长国油版雕一样。2004年的个展后反响也不错,尽管在内容、形式诸方面力求创新,但现在看来整个展览缺少让人津津乐道引领之作。
一个偶然的机遇,创作了行草书八尺四条屏《苏辙<黄州快哉亭记>》。关于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我在《创作自解》中是这样写的:“一件作品,无论尺幅大小,都讲究一气呵成,此八尺四屏却是例外;第一幅写完,发现‘江出西陵’误作‘西出江陵’,意兴都失,弃置一旁。数月后偶然捡出,却有不少可取之处,遂有补足之想。然所用纸乃荣宝斋旧藏,百五十元一张,仅余三张,再无替补,筹思之后,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奋然书之,书后一并张挂,却也气贯势连。惟开头四字,挖补欠佳,是一遗憾。佳纸既尽,笔亦退役。”对这件作品,看法尽管不尽相同,但基本上是持积极肯定的态度,我自己也认为它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自己艺术创新的追求。它给人的启示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用笔的独特性。我用的是一支用颓了的长锋兼毫,一支很普通的毛笔,但弹性还好。书写中,笔毫岔尖,形成破锋,然而通过一定方法的控制,反而形成了独特的用笔效果。刘艺先生认为:“笔毫一分为三仍能使转自如。”曹宝鳞先生评之为:“放旷恣肆,驰骤合节,其焦墨破锋尤为警拔,足称子由‘变化倏忽动心骇目’八字焉。”周永健先生说:“张海先生行草善用破锋,独取一格,盖家数自成矣。域中涉此而善运者寡也。”
二是结构的开合变化。由于驾驭颓锋,必须加大提按开合的力度,从而体现了结体的超常变化。加之在行笔过程中,笔锋时聚时散,从而形成结体或敛或纵的特殊效果,使此篇作品在结体上出现许多出人意料的精彩之处。李刚田先生指出:“张海先生书以气势胜,不拘泥于点画细节之间,然而非精熟无以生气势也。先生笔下游刃恢恢,故举重若轻,有风樯阵马之势。”
三是创作心态的自由、奔放,心无滞碍,任情挥洒,酣畅淋漓。惟心能不滞于物才能进入艺术上自由创作的化境。正像周俊杰先生所说:“我相信,他写此幅作品时,技巧本身已不再是考虑的重点,文学内容也退居后面。他只听见笔与纸摩擦而出现的令书家怦然心动的沙沙之声,只看到笔锋在纸上的奇妙舞蹈,提按使转,横竖撇捺,正侧逆施,八面出锋,艺术家完全沉浸在令毫颖任意挥洒的快意之中。”
在草书尤其是大幅草书的创作中,正确处理好字形与气势、文字内容与艺术形式、感情宣泄与理性书写的关系,是一个至今尚在探索之中的问题。有人以大草作品往往文字难以辨识影响识读为由,对之加以诟病,而点画分明,一丝不苟地理性书写则很难表现行草书的气势。我个人秉持这样一条原则:草法有源,笔法无定,心与冥运,指与物化。写出来的作品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经过近五六年的实践、探索,潜移默化,逐渐成熟。清人刘熙载云:“草书比之正书,要使画省而意存,可于争让向背间悟得。欲作草书,必先释智遗形,以至于超鸿蒙、混希夷,然后下笔。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有以也。”(《艺概·书概》)三地巡展中,按照这一思路创作了一批草书作品,包括一些少字对联,如“退一步想,留几分心”等,都得到了观众的广泛肯定。
当然,就行草书而言,仅仅靠一两种相对极端的风格以图吸引眼球也是不行的。还必须有多种风格作为衬托,使你的行草书表现手法更加丰富。如果说那种激情奔放的作品能把人带入情感高潮的话,那么人不能总生活在高潮状态,还需要多种多样抒发感情的方式。一种书体写出多种风格,这也是一个书家必备的能力和素质。
三、创作解析
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独特艺术语言,这种艺术语言的载体即形态各异的点画,其不同变化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特色。
艺术语言风格一经形成,要让观众感受到其变化绝非易事。认同更不易。其难在一,习惯成自然,要改特难,更弦易辙的前提是对于书法艺术真谛的把握和技艺的高度纯熟;二,变化不是随心所欲,心血来潮,所变应是各种技法相对成熟,有规律可循。
纵览我的行草书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六种不同的风貌。
一、以范仲淹《岳阳楼记》、宋濂《送天台陈庭学序》为代表。这类书作,以点画精微,结构严谨,闲雅舒缓,平正典丽,其风格和审美趣味接近帖学。可以说这类作品是我小行草书的延伸和放大,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前些年创作的《八大山人记》也属于这类风格的作品。
二、以陆游《烟艇记》为代表,特点是老辣苍劲、意象浑茫,介于狂放与严谨二者之间。用笔生涩凝练,结构则讲究意到便成,逸趣天成,不工之工,通篇气象浑融,整体感很强。此种风格最早见雏型于1998年作品集中的《洛阳女儿行》,后经不断探索改进,渐趋成熟。2004年张海书法艺术馆开馆,我创作了这幅《陆游<烟艇记>》,此作品现藏偃师张海书法艺术馆。
三、以《西湖五月半》为代表。这种风格精劲健爽,风骨铮铮。杜甫诗云:“书贵瘦硬方通神”。在书法的传统审美观中,骨力仍处于首要的位置。后人评价王羲之书法:“韵高千古,力屈万夫”,可见骨力对于任何风格的书家都是不可缺少的。这类风格的作品表面看似乎像硬笔书法,然而它是用柔软的毛笔写出来的,因而特别讲究腕力和极强的控笔能力。其雏型见于2003年的作品《屈原(渔父)》。那幅作品不过百字左右,本次展出的则是八尺四条屏,字数也多得多。在如此大篇幅的创作中,保持行笔如精金屈铁、爽朗劲健,非有深厚的功底和长期的训练是无法办到的。这类作品在大型展览多数作品笔酣墨畅,龙飞凤舞的大背景中,以其峻爽冷艳的品格平添几分清新之气。
元曲选册页,与《西湖五月半》、《渔父》有异曲同工之处,峭拔险挺,多姿多彩。
四、以破锋行草书苏辙《黄州快哉亭记》为代表。此类书作特点如前不再赘述。此类书在创作时尽量注意破锋应是水到渠成的创作流露,聚散互用,聚多散少,倘若通篇全是散锋,字字乱麻一团,就难以给人美感。其次是把握墨色的浓淡,过浓过淡都不易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三注意内在气息的畅达,虽有多次停顿调整笔锋,但应笔停气不断,浑然一体;另如《元好问临江仙》、《李白庐山谣》、对联《退一步想,留几分心》、《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等,也各有特色。
五、一笔草风格的作品。关于一笔草,外界有些误解,有人认为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的笔墨游戏而已,其实不然。我在临习古人如王献之、张旭等人作品的时候,发现前人在书写快意时,蘸一次墨而书写数字,直至墨尽笔枯,想见其一任挥洒的快意,十分神往。但那大都是数字而已(见图)。于是我想:草书是最能抒发感情的书体,兴来不可遏,数字岂能尽兴!如果把古人无意间偶然出现的不蘸墨连续书写效果再放大一些,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境呢?于是我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实践。过程并不顺利,曾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也走了不少弯路。所用的材料很重要,什么样的纸、什么样的笔,写出什么样的效果,不经过多次试验是难以把握的。一般认为薄纸吸墨少,其实不然。还有笔,笔太粗不易操作,笔太瘦而吸墨太少。总之经过多次实验,终于可以写出一首七律了。最早是在河南省书画院展出的一张八尺屏条。作品本来是不卖的,但展出当天就被一位画家以不菲的价格收购,可见这类“墨戏”的作品还是有人喜欢的。
一笔草作品最早发表于1995年,徐本一先生认为用笔有些单调,我也同意他的看法。后来在笔法的丰富上动了不少脑筋。在2004年北京中国美术馆的个展中也展出了此类作品。刘艺先生在评论中提到我的一笔草。若论这类作品的局限,那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一笔到底的书写方式本身限制了许多技巧的发挥,因而不可能期望它能多么完美,然而在行草书的大家族,它毕竟是其中的一个样式,一种手法。在一个大展中,有一两件这类作品,能为观者的视觉感受增添几分丰富性,作为展览效果的一种调剂,应该是有胜于无吧!当然,像一笔草这样的作品,是永远不可能成为展厅主流的。
一个规模较大的个展,一种书体要有一两种与众不同的、面貌独特的看家风格样式,一般观众能分得出来、又能够欣赏的风格样式。如果再有一些探索性的形式则更好,不论这种探索观众能否普遍认可,都不会影响展览的整体效果。——当然这里讲的只是形式。不言而喻,形式是次要的,作品的艺术水准才是第一位的,不可本末倒置。
一笔草作品以欧阳修词为代表。
六、小字行草书作品。此种书体自一九九二全国第五届书法篆刻展高票获奖之后,迄今已近二十年。二十年来,虽然事多且杂,然一刻未敢怠懈,检点此类创作的大小册页达数十本之多,倒也欣慰释然,对于小字行草书的获奖及其之后创作的认识,在1998年出版的《张海新作选》的注解中,有一段描述:
1992年五届全国书展,余以赴日未获参与评选,因具被评奖之资格,然亦同于众人,必斩关夺隘而后乃得出线也。彼时之心,岂无惴惴,倘遭黜落,如众口何!而所书小字行草横披,谬承青睐,忝列奖项,四十八人,同膺一时之荣,幸何如之。自兹以来,凡作小字行草,无不指挥如意,心手双畅。甚矣小行草之难也。老者作此,困于自力,少者作此,未得机括,余则适逢其时也。自谓尚不失清雅俊逸,虽非夫人,亦非婢子,其小家碧玉乎!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小字行草书的认识、创作也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从元曲选、唐诗论,自作诗册、论书画诗十首,以及若干扇面等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
我之将小字行草书单列,是我认为它已经具备了个人的风貌。而这种风貌的形成是多年实践的结果。有的年轻作者认为能写大字就必然会写小字,会写小字,一定能写好大字,只要自己实践一下,或者观察一下周围的大量作者,就知道这种结论失于偏颇了。事实上大字和小字不仅是个头大小的区别,二者之间从书写技巧到抒情方式各方面都有本质的不同。因为二者的创作心态和审美旨趣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写小字是一种冷心态,书写时求精求严,理性多于感性。而写大字则是一种热心态,热情奔放,任情挥洒,不计工拙,其时感性多于理性,苏东坡说:“具衣冠坐,敛容自持,则不复见其天。”《庄子·列御寇》云:“醉之以酒以观其则。”前者可用之于写小字,后者可用于写大字。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小字也可以见性情,大字也可以观法度,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目前书法界关于大字创作和小字创作的研究,还是不够的。古人在书论中也只是零星地提到过。如苏轼曾说:“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还有一种说法是:“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令大。”这里讲的只是结字法,但就是这样,后人也提出过质疑。莫云卿说:“自后人伪作右军之言曰‘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张颠引以教颜鲁公,遂作千古谬论。末世又以出自鲁公,不敢置吻;鲁公而后,竟无一人超越自诣古人者。自米元章出,独见此意而自运不足,然谓鲁公书法入俗,可谓具法眼三昧也。”(戈守智《汉溪书法通解》)这里的观点,是不同意把小字当大字写,或把大字当小字写的。然而说的只是结字一个方面,我希望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