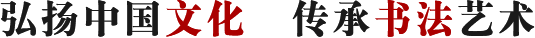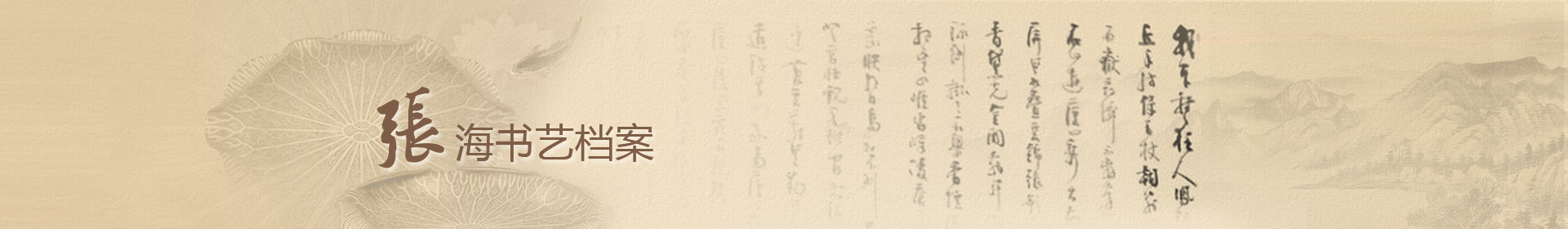适我无非新
——张海创新精神之启示
摘 要:当代书坛领军人物张海先生数十载辛勤笔耕,上下求索,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以卓越的成就名扬上京,誉饮海外。张海的成功对繁荣我国艺术事业多有深刻的启示,这种启示笔者认为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根植艺术传统,传承民族文化,高扬时代精神,表现自我个性。
关键词:张海书艺;创新;艺术传统;民族文化;自我个性
日月常照而辉光日新,草木常荣而姿容异美。新与美是大自然向人类展示的最为华彩的一面,同时又为其运行变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艺术是人类心灵之花的物化,多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结果。美是艺术的本质特征,新为艺术的发展趋势,二者相互依存,不可或缺。书法作为表现民族精神与生命情调的高雅艺术,同样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易·系辞下》)的产物,尚新尚美是其发展繁荣的内在动因。北国书家张海先生,与书艺结缘垂六十年,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以卓越的成就奠定了他在当代书坛的重镇地位。张海走过了一条艰辛而漫长的探索之路,他的成功对推进我国艺术事业的发展启示良多,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如下四方面:
根植艺术传统。书法为华夏民族最为抽象同时又最具活力的传统艺术,就其长盛不衰的魅力而言,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种艺术与之伦比。当然,有人说近代以来日本对书法极为重视,名家辈出,东南亚乃至西方的某些国家对此亦多有研究,但这些都是流而不是源,它的根永远深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书法一要文化,二要技法,二者都来自于对传统的继承,继承传统的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书法是一种尚技的艺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考察,深深植根于艺术传统是张海成功的秘诀之一。张海的艺术思想颇多远见卓识,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那就是“一厘米”论。论及书法的创新,他说:“只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一点新意,哪怕只有一厘米,就算成功了。……世界纪录二·四○米,你能跳二·四一米,就算是一个新的纪录。”[1]这个比喻形象而深刻,书法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人格修养的综合表达,不从传统中充分汲收养料,就不可培育出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古人的成就犹如在我们的面前耸立着一座座高山,我们必须踩着前人的肩膀继续攀登,不可在平地再建一座高台。这“一厘米”非同寻常,是来自传统而又高于传统的一厘米。前贤既重传统,又重创新。唐代书家李邕在艺术实践上极富创造力,他“初学右军行法,既得其妙,复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2]启功先生说:“创新必须是继承前提下的创新。”[3]述而不作无创新可言,张怀瓘说:“与众同者俗物,与众异者异才,书亦如然。”(《书论》)唐朝释亚栖说:“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4]张海的“一厘米”论,应为继承与创新的最佳表述,是高标准而非低标准的,是从传统中来而又努力超越传统的。改革开放后中华大地春风浩荡,艺术繁荣,书风之变化可谓晨奇暮诡,取得了一定的实绩。然而进行理性审视,我们清晰地看到当代书坛受日本前卫派书法和西方现代主义画风的影响甚深,有人对传统技法予以卑视,尚趣之风颇为盛行。从艺术发展的轨迹而言,这些中青年书家的探索精神不乏可取之处,因为他们在求新求变,力求达到一种超越。但他们的实绩甚为有限,求拙的少,求巧的多,不够厚重,比较浮华。书法是古老艺术,传统的根太深了,中国书艺的发展,很难像西方现代主义绘画艺术一样可以中断传统而另辟蹊径。其实,西方现代主义也讲传承,曾从中国书法汲收了不少养分,而今要影响中国书坛,试图动摇其根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张海强调根植传统而求新变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时尚的东西来得快,流行得快,消失得也快,而根植于民族艺术传统的东西能传之久远,这应该成为现代书艺追求的终极目标。
张海的创作实践了他的艺术主张。论及张海艺术创新所取得的成就,沈鹏先生说:“杰作之所以为杰作,就好在它光彩照人,一新耳目。……作品开辟了一个新的格调,用笔如屈铁,如游丝,布局成行不成列,萧散而严谨,空灵又凝重。这是在长期探索之后多种条件齐备时出现的必然中的‘偶然’,有意中的无意。”[5]张海对传统的继承可谓殚精竭力。他自幼痴迷书法,故乡河南偃师曾养育过颜真卿、王铎等书坛巨匠,中原文化的沃土使他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将浓厚的兴趣建立在一点一画的基础功夫上,单是汉碑,《乙瑛》《史晨》《曹全》《礼器》《张迁》等都一一临写,几夺其神韵,直到专注于《封龙山碑》。随着研究的深入,他的语言更加丰富,他以二王为法,兼收唐之旭素,宋之米黄,明之铎山,清之邓赵,融化淬砺为自己崭新的艺术语言。他有一首诗形象地描写了书家走过的积学专精、整合创新之路:“许身何必效羲献,朴茂雄强亦可宗。博取百家求一是,吉金汉简化封龙。”张海的隶书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其疾风劲草般的草隶中,娴熟自如,化繁为简,抛弃了不少隶书原有的波磔和蚕头雁尾,扩展和延伸出一种时而像脱缰野马,任由驰骋,时而像扬鞭快马,陡然生风的独特风格。随着隶书的突破也带来篆楷行草的整体推进。张海将飞白这一古老技法嫁接于自己的艺术语言之中,增添了书品的动感和诗意,可见张海对传统的扎根是何等之深。张海喜作长帧巨幛,多有一种雷霆万钧、海雨天风的磅礴气势,这固然与他的才力和艺术胆识有关,而很可能受王铎的影响颇大。王铎追求雄劲苍峻的书风,而不因袭二王书法的“不激不厉”,他的临帖也别具新意,常常将古人尺牍尤其是二王的案头小幅临作四尺、五尺甚至八尺悬壁大幅,变小字为大字,增强表现力。[6]张海的布局受黄道周、邓石如的影响甚深,但他的取法前贤,已完全遗形取神,不着痕迹。
传承民族文化。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它是赖以延续发展的精神支柱。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江溶在《中国文化大观系列》总序中说:“文化者,民族灵魂之光也。……文化之创造,诚当日新其法,通其变以不倦;月新其视,刚健笃实以辉光。”书法作为华夏民族独有的高雅艺术,之所以为人民大众所钟爱,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是因为以独特的艺术形式传承了中华文明。书法创新的路子不管怎么走,但一点可以绝对肯定:它必须以传承民族文化为旨归。英国艺术评论家赫伯特·里德论绘画艺术时指出:“从作品的线条中,我们便可窥探出艺术家与他所处时代的文化之间的关系。” [7]书法的困难在于:必须用最雄厚的文化积累来作最简单的抽象表达。张海创新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传承、弘扬本民族文化方面已竭尽心力。“文化”的内涵甚为宽泛,关于书法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当代学者欧阳中石、葛承雍等先生作了广泛而深刻的论述。笔者所谈的文化是狭义的,仅从文学、哲学、美学的层面而言。书法与文学的联系最为密切,一个书家的文学素养不可或缺。古人特别注重书法的书卷气,宋代诗僧佛印说苏轼因为“胸中有万卷书”,故“笔下无一点尘土。”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工的日益精细,书法逐渐走向专业化,于当代书家若一律要求博学如苏轼、赵孟頫、郭沫若、启功等人,的确有些苛刻,然而真正的大家至少应对文史哲有较深的造诣。我认同陈振濂先生的观点:“一个第一流的书法家,可以不是画家、不是政治家、不是经济家,但却必须是诗人、文学家。”[8]张海所学专业虽非文科,而数十年来孜孜以求,对文史哲的博通非同寻常。细读张海不同时期的书法精品集,大多书品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有的诗作佳什,连从事文学研究的专家也很少读过,可见张海对文学的研究是广泛而深入。细读每幅书品,书家对原作情感的理解与把握也恰到好处。吴振锋先生在欣赏其行草书代表作《苏辙·黄州快哉亭记》时指出:“(书品)神怡务闲的自由心境与苏辙‘随缘自适’怡然而乐的自得相形益彰,和谐统一。”[9]张海的自书诗、自撰联,书境与诗境往往浑然一体。张海的文章颇具特色,如行云流水,晓畅自然,清丽简练。尤其是用文言写的散点观照式的评论,深刻优美,凝练畅达。张海的书风、诗风、文风均以自然为高,无夸饰之心,湛发出一股清气、逸气。
书法作为华夏文化的艺术载体之一,自然是以中国古典哲学、美学作为其思想内核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感觉到它的博大精深。笔者认为,张海的书艺,深刻地表达了以儒学为代表的文化精神。这可从三方面略加窥视,其一,阳刚博大的风格。以《易经》为代表的儒学精神,则天法地,体现出阳刚博大的美感特征。《乾·彖辞》:“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坤·彖辞》:“坤厚载物,德名无疆。”古人仰观俯察,见日月之高明,大地之辽阔,品类之丰盈,感觉人类应象天地一样包含万象,自强不息。孟子强调要颐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这表现于艺术意境之中,自然是阳刚壮美,博大雄强。张海的书品,大气磅礴,有一种高天揽月的气势,其思想内核无疑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甚深。张海对崇高之美的追求,很可能直接受颜真卿的影响。颜鲁公的人品书品历来为人称颂,几乎取王羲之而代之,沈作喆说:“予观颜平原书,凛之正色,如在廊庙直立鲠论,天威不可屈。”(《寓简》)颜鲁公是以儒学立身的杰出书家,作为乡先辈,他对张海的影响是彻入骨髓的。其二、尚中和的美学理想。《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和是儒家哲学追求的理想境界,张海明确提出书艺境界应崇尚中和之美:“作苍老则神失遒润,不激不厉则迹近中庸,至若苍老而不失童子心,中庸而可以蹈白刃者,吾虽不敏,正欲求之耳。”(《张海新作选》第三十五自解)张海书风刚而不戾,秀而不媚。其三,高雅的艺术旨趣。儒家的美学理想以典雅为高。艺术本来是雅事,是高情雅意的物化和外化。儒家特重修身,追求一种端庄文雅的气度美。因此孔子品人强调“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品艺强调文与质的和谐统一,以纯正典雅为高,故论诗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张海的艺术创新,尚奇、尚变、尚气、尚法,但又高雅脱俗。读他的书艺,可以说每根线条、每个结体、每篇布局均有来历,既典雅纯正而又充满现代气息。他的创新,没有故作前卫之高蹈,不搞聚墨成形、信笔为体,而严格遵守汉字的书写规律和美学要求,朗现出一种高雅的美。当然,张海书境的空灵、飘逸,与庄禅的境界也是暗通声气的。张海的书艺体现了以儒家为主体并兼融佛道的美学精神。传承民族文化的艺术才是高品位的艺术,当然,我们这种传承应注意到中华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我们应不薄今人爱古人,不薄西方爱东方。
高扬时代精神。艺术是艺术家生命本体的物化,同时也是时代精神的折光。人是社会的产物,艺术不可能超越时空。书法虽有较大的抽象性,但一种风格的形成无疑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丹纳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10]一个书家的审美观念总会受到时代风气和潮流的影响制约,必然会表现出对创作主体精神境界的推崇。秦汉艺术的博大雄强,那种生机勃勃的野性美,无疑是气势恢宏的时代精神的形象表达。魏晋的钟、王书法达到了萧散简远的最高成就,在他们的书法里体现了身心俱遣、物我兼忘的境界,这种风格的审美要求,显然是老庄忘情于世道、把现实的人生完全淡化的哲学思想在艺术上的复现。论及晋人的行草,有人认为其形态荒率朴实、章法气韵流畅自然的特点及其所造成的韵律感和动荡感的效果,恰好表现出晋人表面风流儒雅、潇洒飘逸,内心却充满忧危恐惧、哀怨不平的心理与情绪。[11]唐代是中国书艺发展的黄金时代,法度的完备,风格的鲜明性、多样性均为后人难以企及。论及唐代书艺发展的内在动因,李泽厚说:“那如走龙蛇、刚圆遒劲具有弹性活力的笔墨线条,那奇险万状、绎智遗形、连绵不断、忽轻忽重的结体、布局,那倏忽之间变化无常、暴风骤雨不可遏制的情态气势,盛唐的草书不正是这纸上的强烈舞蹈么?绝句、草书、音乐、舞蹈,这些表现艺术合为一体,构成当时诗书王国的美的冠冕,它把中国传统重旋律、重感情的‘线的艺术’,推上又一个崭新的阶段,反映了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上升阶段的时代精神。”[12]盛唐文化充满阳刚之美,充溢着豪放雄强的进取精神。艺术创新,若不能表现时代精神,不能高扬时代的主旋律,那么要有重大突破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时代是最富活力、最富开拓精神的崭新时代。刚健清新的艺术更能振奋国人的精神,鼓舞人们在历史的征途中奋然前行,张海的创作牢牢地把握了这一点。张海的创作,始于实用美术,而又摒弃俗笔,在理智之光的牵引下,将满腔激情化作静如处子、动如英豪的线条,在黑白浮动的世界中,终于登上至高的境界:其书正草篆隶如秦始皇兵马俑布阵井然,远看气势恢弘,肃穆古远,而其浩然正气,使人遥想千载文化之灿烂,呼吸中华文明之气息;而近看钩画了了,神采奕奕,灵光四射,美不胜收。张海的书法点画掷地有声,斩钉截铁;线质铿锵有力,承接了碑派的威武气派,金石的苍茫气,再现了金戈铁马的宽博气象;而线情,由于飞白的造像,使得它神采飞扬,如西湖女子,凌空舞袖,一展帖派之柔情。张海的书法体现着一种健美,一种正大气象,一种时代的阳刚之气。那种力感,那种气势,那种激情,让人感觉到时代的铁流在汹涌,东方的巨龙在高翔。张海的书艺,力与美达到了有机结合,既给人以力量的鼓舞,又给人以心灵的慰藉。张海的书艺以崇高为宗,已逼近雄浑境界。何谓雄浑?司空图作过如此描述:“大用外腓,中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诗品》)扬振纲说:“此非有大才力大学问不能,文中惟庄马,诗中惟李杜,足以当之。”(《诗品解》)。于书艺而言,笔者认为汉之碑版,唐之行草,清之篆隶,那些大家们的风情骨力大多逼近雄浑境界。而张海生河清之盛世,积渊深之学养,蓄浩然之正气,淬精湛之技艺,发而为书,其清雄刚健之书风与昂扬奋进之时代精神已忻合为一。当然,我们强调艺术应高扬时代精神,这与追求风格的多样统一并不相悖。崇高与优美均可表现时代精神,同是崇高,因每人的气质、学养有别而风格显然各异。
表现自我个性。山林中绝无完全同形的两片树叶,江河中绝无完全同质的两处流水,书艺也是如此。书法的个性大多表现为独特的风格和凭借审美意象表达的丰富情感。书艺进入极高境界方可能达到一种抒情的自由。孙过庭强调应把书法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并将这一特点提到与诗歌并行、与自然同美的理论高度:“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书谱》)其实,单就文字的符号性质而言,每个人的笔迹绝无雷同,这通过科学仪器作出鉴定,但这不能证明每个人的书法都有个性。书法不同于写字,它要求表现美,要表达特定时空中的情感,既为孤吹,又谐众耳,这才能称之为独特风格。关于这一点,近代美学大师王国维说:“夫绘画之可贵者,非以其所绘之物也,必有我焉以寄于物之中。……其于书亦然:石田之书,瘦硬如黄山谷;南田之书,委媚如褚登善。而石田之书,又非登善、山谷之书也。彼各有所谓我者在也。”[13]这里的“我”,应为艺术家独特的个性。独特风格的形成是成熟书家的标志,而多样统一书风的形成应为艺术大家的标志。风格的形成,情感的表达,又依赖乎审美意象,论及情感与意象的关系,朱光潜说:“情感是生生不息的,意象也是生生不息的。换一种情感就是换一种意象,换一种意象就是换一种境界。”[14]当今,我国书法事业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有些先生心多浮躁,不能静心为学,艺术语言单一贫乏,艺术功力还很难追蹑情感的运动,追风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学某人,学某体,赶潮流,希冀在最短的时间里成就辉煌事业,这种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不可能在创作领域有所突破。诚然,艺术不可能完全超于功利,而进入较高境界又必须超于功利。其实追风现象并非始于今日,古已有之,宋代颇盛。韩琦好颜书,士俗皆学颜;蔡襄贵,士庶皆学之;王安石作相,士俗又学其体。[15]其实追风只能当作临贴与读贴,并不能代替高品位的创作。重复前人,重复名家,重复自己,将导致艺苑黄茅白苇,一派荒芜。
张海的艺术创作体现了鲜明的个性。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书法语言既博涉兼融,又词必已出。语言是构成风格的本体元素,杰出书家必有其独具个性的的艺术语言。张海能以开阔的视野,深邃的目光,宽厚的胸襟,广采博取又精嚼细咽,最终化为得心应手的创造,体现出大师的学养与功力。艺术多有相通之处,由张海的治艺方法我想到了袁枚的一段精彩论述:“文尊韩,诗尊杜:犹登山者必上泰山,泛水者必朝东海也。然使空抱东海、泰山,而此外不知有天台、武夷之奇,潇湘、镜湖之胜,则亦泰山之上一樵夫,海船之上一舵工而已矣。学者当以博览为工。”[16]如前所述,张海从汉碑入手,得力于《封龙山》,又饶简牍自由灵动之真趣,成功地将碑派与贴学融为一炉,熔铸而成汪洋恣肆的饶有个性的语言。他既不重复别人,也尽可能不重复自己。张海在谈到草隶创作时说:“创作中要求自己写的东西多些,努力克服传世碑刻本中斧凿刀刻的痕迹。为此探索之后,使自己的作品,在朴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天然,流畅的成分。”[17]其二:追求风格的独特性与多样性和谐统一。张海的主体风格是清雄刚健,但因书体不同,书品内容和创作时的心境有异,每幅作品多能体现出一定的个性。张海的整体风格是由于多年习碑养成的雄劲大气,简捷流便。读其隶书七条屏所书的岑参诗,恣情任性,挥洒自如,字形结体端庄伟岸,气度开阔稳健,规整与奇谲并出,雄强与秀美兼得。近年来,张海行草书的成熟还超过了隶书,他以简隶书为母本,参用碑派用笔的厚重浑朴和帖派用笔的活泼灵动,以及大篆线条的圆劲古厚,既可读出米芾的爽利骏发,董其昌的圆转流利,更可以读出王铎、张瑞图的方峻劲折。张海时而浅笑,不乏莞尔嫣然之妙。其三,强烈的抒情色彩。书法是张海唯一终生不渝的兴趣爱好,他为其倾注了毕生的全部激情,表现出一种刻骨铭心的爱和“甘冒斧钺”的献身欲望。他的不少佳作多已臻至尚情尚意的唯美境界。他的字个个都是写出,并非画出。只有“写”出来的字,才有个性,才有笔情墨趣。张海的行草书这种抒情性尤为强烈,他谈过这样的感受:“每当我引笔挥洒行草书时,一扫隶书创作时的平静心态,热血沸腾,思绪奔涌,笔随意转,行于当行,止于当止,自觉一任感情的澎湃,笔下自然多姿多态,生气勃发。”[18]艺术创作臻至心手双畅,无意于佳而自佳的抒情境界,这是技法、学养、才情已达到完美统一的综合体现。
王羲之《兰亭诗》云:“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张海的书艺新如雨后之苍松,美如溢彩之琼瑶,读来把人带入如沐清风,如濯清流,如饮醇醪的艺术意境之中。张海的成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艺术创作必须根植传统,必须传承民族文化,必须表现时代精神和自我个性。创新是艺术的生命,但技艺工妙是根本,同时应克服创新的盲目性与随意性。艺术境界主于美,求新求变而不求美的艺术,产之再多也不过是林中散木、园中杂草而已。艺术的新美源于主体的充实,毛泽东诗云:“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送纵宇一郎东行》)由此观之,真体不充,技法不精,目光不远,创新之路将是南辕北辙。
参考文献:
[1]《学书三问》,《张海书法作品选》(2004-2005),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
[2]《宣和书谱》,转引自欧阳中石等著:《书法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307页。
[3]张志和编:《启功谈艺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17页。
[4]转引自葛承雍:《书法与文化十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113页。
[5]西中文主编:《创造力的实现》,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3页。
[6]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库:何学森:《论行书的形成与风格演变》,第105页。
[7]赫伯特·里德:《艺术的真谛》,王柯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37页。
[8]陈振濂:《书法美学教程》,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9页。
[9]《张海行草书佳作解析》,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32页。
[10]同[2],第154页。
[11]同[4],第77页。
[12]李泽厚:《美的历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35页。
[13]《王国维论书法艺术》,见萧艾:《一代大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52页。
[14]朱光潜:《谈美》,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112页。
[15]同[2],第402页。
[16]袁枚:《随园诗话》卷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版,第266页。
[17]同[5],第195页。
[18]转引自:刘宗超:《理性与激情的碰撞》,同[1],第147页。
(作者蒋力馀:男,湘潭大学附中高级教师,湘大艺术学院兼职教授,书画评论家。蒋正治:男,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陕西商洛学院教师。)